意識理論家們經過長達五年的「對抗性合作」,成功呈現了一場在觀眾面前的舞台對決。儘管這場對決沒有決出最終的勝負,但這仍然被視為科學史上的一次進展

#在科學屆,理論往往層出不窮,但是經過資料的拷打後,保留下的只是少數。在剛起步的意識科學中,主導理論尚未出現。 20 多種理論仍然在這個舞台上較量。 這現狀倒不是因為缺乏數據。自從DNA 雙螺旋的共同發現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三十多年前將意識作為研究主題以來,研究人員一直使用各種先進技術來探測受試者的大腦,追踪可以反映意識的神經活動特徵。到目前為止,產生的大量數據至少應該已經打倒了那些站不住腳的理論。 五年前,鄧普頓世界慈善基金會(Templeton World Charity Foundation)發起了一系列對抗性合作,以推動理論篩選工作的進行。今年 6 月,這項合作的第一個結果是,將兩個備受矚目的理論相互對立:全球神經元工作空間理論(GNWT)和綜合資訊理論(IIT)。兩種理論都沒有成為最後的贏家。 這一結果就像在紐約舉行的意識科學研究協會(ASSC) 第26 屆會議上宣布的賽事結果一樣,也被用來結算克里克的長期合作者、神經科學家、艾倫腦科學研究所的Christof Koch 和紐約大學的哲學家David Chalmers 長達25 年的賭約,後者創造了“難題”(the hard problem)一詞來表述人們可以透過分析大腦迴路來解釋意識的主觀感覺的假設。 
#
艾倫腦科學研究所中的神經學科學家 Christof Koch 認為,對第一次意識對抗合作的融合是科學的勝利。 在紐約大學Skirball 中心的舞台上,在搖滾音樂、關於意識的饒舌表演和一系列研究結果的展示之後,Koch,這位神經科學家向哲學家們打賭說:意識的神經相關性目前還不能確定。 但確實如此嗎?該項目獲得的評價褒貶不一。一些研究人員指出,目前還未能對兩種理論之間的差異進行有意義的測試。但其他人強調了該計畫在推動意識科學前進方面的貢獻:提供大型、新穎、規範的數據集,以及激勵其他參賽者進行自己的對抗性合作。 #當克里克和Koch 在1990 年發表當他們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邁向意識的神經生物學理論》時,他們的目標是將意識——2000 年來都被哲學家佔據主場—— 置於科學基礎上。他們認為,整個意識是一個過於寬泛和有爭議的概念,不能作為根本的起點。 相反,他們專注於意識的一個科學可處理的方面:視覺感知,也就是在有意識的情況下獲得視覺訊息,例如,紅色這種顏色。他們的目標是找到與這種現象相關的神經,或者正如他們所說,意識的神經相關性。 解碼視覺感知的第一階段已經是科學研究的肥沃土壤。落在視網膜上的光線向大腦的視覺皮質發送訊號。在那裡,超過 12 個不同的神經模組處理與影像中的邊緣、顏色和運動相對應的訊號。他們的輸出結合在一起,為我們所看到的東西建立了最終的動態畫面。 視覺感知對克里克和 Koch 的價值在於,這條鏈中的最後一環 —— 意識 —— 可以與其他環節分離。自 1970 年代以來,神經科學家已經知道有盲視(blindsight)的人,他們因為大腦受損而沒有視力,但他們可以在房間裡導航而不會遇到障礙物。雖然他們保留了處理圖像的能力,但他們失去了意識到它的能力。  在這個著名的幻覺圖片中,大腦產生意識的機制允許我們以花瓶或兩張臉的形式體驗圖像 —— 但不能同時體驗。 --Nevit Dilmen
在這個著名的幻覺圖片中,大腦產生意識的機制允許我們以花瓶或兩張臉的形式體驗圖像 —— 但不能同時體驗。 --Nevit Dilmen
我們所有人都可以體驗到這種脫節的形式。舉一個眾所周知的光學錯覺,上圖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花瓶或兩張臉。在任何時候,我們只能把它看作是一個或另一個。我們的大腦處理感知的方式阻止了我們同時意識到兩者。 實驗心理學家可以透過雙眼競爭現象來利用這種脫節。我們的大腦通常可以毫不費力地結合它從左右眼收到的略微不同的重疊影像。但如果圖像非常不同,而不是合併,它們就會成為競爭對手:首先一個圖像主導我們的感知,然後輪到另一個圖像。當馬克斯・普朗克生物控制論研究所的神經科學家 Nikos Logothetis 在 1996 年描述雙眼競爭現象時,克里克非常興奮,他宣稱意識的神經相關性將在 20 世紀末找到。 (這種熱情促成了Koch 與Chalmers 的賭注。)#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大腦掃描儀做的越來越複雜,受試者的感知在意識研究期間已經能被操縱。數據的涓流已經幾何倍增長,但河裡存在意識理論不僅沒有被沖走,反而是倍增。 這些理論之間的一個劃分方法是,其中一些理論,如GNWT,認為意識需要大腦中實現認知部分的參與,也就是我們「思考」的地方,而IIT 理論研究者和其他人聲稱,神經相關性取決於參與感知的大腦區域,也就是我們「感覺」的地方。這些想法通常被直觀地描述為「大腦前沿」理論與「大腦後腦」理論(儘管實際的解剖學區別比這更不準確和枯燥)。這種耐人尋味的區分呼應了古爾的舊哲學分析,即意識到底是與思維有關的,如笛卡爾所說的“我思故我在”,還是“與思考無關”的,如冥想瑜伽那般放空思想。 
##對於GNWT 的堅決倡議者、法蘭西公學院的神經科學家Stanislas Dehaene 來說,思維是意識狀態的核心部分。在提到 IIT 時,他表示:這是兩種理論之間的巨大差異。我不相信存在純粹的意識。
GNWT 堅持認為,我們在無意識地處理訊息時,會有一小部分訊息能透過一個管道進入有意識狀態的工作空間內。在這個空間內,訊息被整合並傳遞到其他大腦區域,使其在全局範圍內用於決策和學習。 Stanislas Dehaene 表示:這個工作空間承擔了執行功能的使命。由於決策和學習是前額葉皮質的責任,大腦的前部被認為對意識至關重要。
這個觀點早在 1988 年就萌芽於心理學家 Bernard Baars 的心中,目前他在心智科學學會工作。他看到了與早期人工智慧系統架構 —— 黑板(blackboard)的相同之處,在黑板架構中獨立程式也能分享資訊。然後,Dehaene 將這個概念模板與尖端神經科學的發現聯繫起來,並使用計算模型來開發 GNWT。
IIT 則沒有與人工智慧架構進行類比。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神經科學家和精神病學家Giulio Tononi 從關於意識的五個公理開始,發展了IIT 這個理論:意識是擁有它的實體所固有的;意識的組成是結構化的;意識的資訊豐富;意識是整合的而不可簡化為組件;意識是獨立於其他體驗的。然後,他開發了數學描述來適應這些公理。對於 Tononi 和其他 IIT 理論家來說,與這些數學描述最一致的神經結構是與感覺區域相關的網格狀架構,他們稱之為熱區(hot zone)。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神經科學家 Giulio Tononi 透過數學公式化五個關於意識的公理,發展了綜合資訊理論。 ——John Maniaci / 華盛頓大學健康中心#但GNWT 和IIT 只是將意識的關鍵元素定位在大腦相反兩極理論中的兩種,時下還存在著其他認知方式的前腦概念,包括幾種高階理論(HOT)和主動推理理論,以及各種後腦概念,例如一階理論和局部表徵理論。 雖然說起來可以透過將活體大腦的數據與理論的預測值放在一起對比是否一致的方法來證偽其中一些理論。但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多年來,研究人員設計了一系列巧妙的實驗,在這些實驗中,受試者報告他們何時意識到一個物體,同時使用一些心理學技巧或幻覺來分散他們的注意力。這些結果表明,意識感知與前額葉皮質的活動有關,這有利於 GNWT 或其他大腦前部理論。但哲學家和實驗者也提出一種質疑說,這些研究可能是在測量與報告任務相關的神經活動,而不是意識本身。 因此,科學研究界發展了無報告範式作為一種解決方法,這就是雙眼競爭。如果測試對象的左眼看到向左移動的臉,右眼看到向右移動的房子,他們的意識感知就會在兩個影像之間翻轉。研究人員可以透過追蹤眼睛移動的方式來識別感知到的圖像,而無需報告。當時的數據表明,在這些無報告範式中,有意識感知的訊號位於大腦後部。 然而,理論家們很少輕易就被實驗和數據所說服。在 2016 年的一次審查中,印度理工學院陣營駁斥了基於報告的實驗,認為其方法上有缺陷。但在 2017 年,這場爭論仍在繼續,《神經科學期刊》上發表了幾篇觀點相互對立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現任職於日本理研腦科學研究中心的 Hakwan Lau 和他的同事反駁道,無報告範式本身就充滿了令人困惑的變數。 更複雜的是,實驗結果取決於所使用的大腦記錄技術的類型。這並不奇怪,因為每種技術都為大腦提供了不同的視角。例如,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可以追蹤血流並提供良好的空間分辨率,但速度太慢,無法跟上神經元之間的交流速度。另一方面,腦磁圖(MEG)可以追蹤大腦的顫動,但空間解析度較差。研究人員是測量大腦特定位置的訊號強度,還是分析更廣泛區域的模式,這也會產生影響。 結果是,儘管收集了大量實驗數據來研究意識的相關性,但不確定性給了理論學家聲稱這些數據支持他們認可的理論的空間。 特拉維夫大學神經科學家 Liad Mudrik 認為,部分問題在於研究的設計方式。她的博士生 Itay Yaron 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研究了 400 多個已發表的意識實驗,發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僅根據實驗設計來預測哪種理論將得到支持,而無需了解任何結果。 
特拉維夫大學的神經科學家Liad Mudrik(左)和她的博士生Itay Yaron(右)收集的證據表明,利用實驗研究來檢驗意識理論的目標常常因實驗設計中潛藏的偏見而受挫。 ——Sophie Kelly五年前,鄧普頓世界慈善基金會特別計畫部負責人Dawid Potgieter 驚訝地發現,關於意識的可行理論仍然如此之多。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應該為此做些什麼。 Koch 建議正面交鋒,物理學有時也用這種方法來解決爭議,心理學界也有先例。 1980 年代,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研究員 Dan Kahneman 創造了 對抗性合作(adversarial collaboration)一詞,用來描述觀點相左的科學家共同發展實驗的做法。透過合作,他們可以消除在目標和方法上的分歧,因為這些分歧可能會破壞工作的結論。 
五年前,Dawid Potgieter 代表鄧普頓世界慈善基金會召開了一次研討會,旨在發展對抗性合作,以檢驗意識理論。 —— 鄧普頓世界慈善基金會Potgieter 很想這樣試試看。 2018 年 3 月,他和 Koch 在西雅圖艾倫研究所為 14 名參與者舉辦了一場週末研討會。其中包括三位理論家——Dehaene、Tononi 和Lau,他們是HOT 的擁護者—— 以及Chalmers 和另外兩位哲學家、四位心理學家、兩位神經科學家、一位神經學家和作為坦普爾頓基金會代表的Potgieter。他們的職責是合作設計新的實驗,以消除過去的所有問題並清晰地區分不同的理論。 其中三位心理學家—— 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Mudrik、Lucia Melloni 和波特蘭社區學院的Michael Pitts—— 已經在過去進行過對意識理論的挑戰。 Pitts 回憶道:突然有一天,我想起 Giulio 建議過,你們三個人為什麼不領導這個計畫呢?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它吞噬了我們的生命。 在接下來的九個月裡,討論仍在繼續。理論家們深入研究了他們的理論,並提出了新的預測 —— 這是合作的新穎貢獻之一。 Mudrik 對對手進行談判的意願印象深刻。她說:這需要很大的勇氣;這是一場冒險。 研究小組想出了兩種實驗設計,以區分 IIT 和 GNWT 的預測結果。他們從未得出足以將 GNWT 和 HOTs 區分開來的不同預測,因此 HOTs 被留給了 Lau 和紐約大學哲學家 Ned Block 的另一次對抗性合作,後者是一階理論的擁護者。 Tononi 對 GNWT 與 IIT 的首次實驗的設計特別重視。由於既定的任務在過去的實驗中造成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因此它將透過改變任務來了解這對有意識感知的影響,從而解決這些問題。 實驗物件將看到一系列不同的圖像,如人臉、時鐘和不同字體的字母。他們看到每張圖像的時間為 0.5 到 1.5 秒。在每一系列圖像的開始部分,有兩幅特定的圖像會被定義為目標(例如,一個女人的臉和一個復古的時鐘),受試者會被要求在看到其中任何一幅圖像時按下一個按鈕。因此,圖像中的其他面孔和物體將與任務相關(因為它們與目標屬於同一類別),但無需報告。系列影像中的其他類型影像,如字母和無意義符號,則與任務無關。該測試使用系列中的不同目標反覆進行,這樣每組刺激都可以同時作為任務相關和任務無關進行測試。最先進的大腦訊號解碼器將把神經發射模式與受試者所看到的內容連結起來。 GNWT 的預測是,無論是否涉及任務,與有意識地感知物體相對應的大腦模式都是相似的。大腦解碼器應該能夠識別與目標影像相關的獨特訊號,與任務無關。此外,還應該能夠檢測到進入大腦工作區的新意識知覺的「點火訊號」以及清除它的「關閉訊號」。 另一方面,IIT 預測大腦的意識模式會隨著任務的不同而變化,因為執行任務需要前額葉皮質的參與,而剝離任務的感知則不需要。這種純粹的意識只需要大腦後部的感覺熱區。圖像意識訊號的連接性和持續時間將與視覺刺激的持續時間相匹配。 
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研究員 Daniel Kahneman 堅信對抗性合作對推動科學發展的價值,儘管他發現合作結果很少改變對手的想法。 ——Roger ParkesDehaene 偏好第二項實驗,涉及大腦模式的綜合解碼。受試者在玩類似俄羅斯方塊的電子遊戲時,會隨機看到螢幕上閃過的人臉和物體。一幅圖像出現後不久,遊戲就會停止,然後詢問受試者是否看到了這張圖像。 Dehaene 更喜歡這種設計,因為它在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心理狀態之間提供了更清晰的對比,他認為這對於獲得意識相關因素的明確數據至關重要。 由於 Kahneman 對對抗性合作非常熟悉,他對三個專案的負責人進行了指導。但他也告誡他們,根據他的經驗,對手不會在看到合作成果後改變主意。他說,相反,當面對一個不方便的結果時,他們的智商會躍升 15 點,因為他們會發明一些方法來適應新的、相互矛盾的數據。 研究人員開始按照研討會團隊的建議進行實驗。 Tononi 最喜歡的 GNWT 與 IIT 實驗(以不同程度的任務進行測試)最早完成。該實驗是在兩個不同的實驗室使用功能性磁振造影、腦磁圖和顱內腦電圖進行的。共有 6 個理論中立實驗室和 250 名測試對象參與其中。 6 月 23 日晚,一群興奮的觀眾聚集在紐約大學,觀摩該實驗的結果。結果顯示在一個巨大的螢幕上,是一張以紅色和綠色突出顯示的圖表,就好像研究人員正在報告具有三個障礙的障礙賽跑一樣。 第一個障礙是檢查每個理論對受試者在呈現的圖像中看到的物體類別的解碼程度。兩種理論在這裡都表現良好,但 IIT 更擅長辨識物體的方向。 第二個障礙是對訊號時間的測試。 IIT 預測在意識狀態期間熱區會持續同步放電。雖然訊號持續存在,但它並不保持同步。 GNWT 預測的工作空間會「點燃」,然後當刺激消失時會出現第二個峰值。僅偵測到初始尖峰。在紐約大學觀眾的螢幕評分中,印度理工學院遙遙領先。 第三條障礙涉及大腦的整體連結性。 GNWT 在此得分高於 IIT,主要是因為結果的一些分析支持 GNWT 預測,而整個熱區的訊號並不同步。 顯然這兩種理論都受到了結果的挑戰。但在活動畫面上的最終計分中,IIT 獲得的綠色亮點比 GNWT 更多,觀眾的反應就像勝利者加冕了一樣。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Melanie Boly 是IIT 的支持者,她對這一結果感到相當滿意,在台上宣布:結果證實了IIT 的總體主張,即後皮質區域足以產生意識,並且「前額葉皮質的參與”也不需要全域廣播。 
法蘭西公學院的神經科學家 Stanislas Dehaene 提出了全域神經元工作空間理論,他認為思考是意識的核心部分。 當 Dehaene 上台時,他也不承認失敗。 「我決定聽從 Dan Kahneman 的建議,」他打趣道。同時他顯得很高興,因為這個實驗最有趣的部分是與任務無關的意識刺激實驗。現在的問題是實驗是否能夠顯示額葉大腦中能夠點燃意識。 「答案是肯定的!」他說。 後來,Dehaene 建議,IIT 的門檻比他的理論設定的門檻低。 [IIT] 的複雜數學核心沒有經過真正的測試,他說。正如 Block 在當晚的演講中指出的那樣,支持腦後理論的發現並不完全支撐 IIT。 儘管印度理工學院獲得的綠色分數略高,但計畫負責人本人堅稱沒有贏家。他們在一篇描述中寫道「這些結果證實了IIT 和GNWT 的一些預測,同時極大地挑戰了這兩種理論。」那麼科學到底進步了嗎?並非所有人都這麼認為。 墨爾本大學心理學家、ASSC 前主席Olivia Carter 等一些研究人員認為,這兩種理論相差太大,無法對他們的預測進行有意義的比較。 「我個人的感覺是他們正在測試完全不同的東西,」她說。 「IIT 專注於現象級內容,而 GNWT 對記憶和注意力更感興趣。」這個評價似乎很恰當。然而,考慮到對抗性合作最初的既定目的是進行決定性比較,這也有些令人沮喪。如果要說這個結果是科學的勝利,那麼似乎只能說是達到及格線而已。 莫納什大學哲學家 Jakob Hohwy 是另一個由坦普爾頓資助的對抗性合作計畫的成員,他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這涉及科學哲學,」他說。他指出,該領域在意識的定義是否更接近思考或感覺,甚至受試者自我報告的結果是否真正混淆了數據等基本問題上仍存在分歧。對 Hohwy 來說,這種協作努力是前進的方式。 「當我們進行這種類型的對抗性合作時,我們將會發現答案,」他說。 其他人,例如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計算神經科學家Megan Peters,對媒體報導感到憤怒,因為媒體將結果報導為GNWT 和IIT 之間的兩匹馬競賽,而不是一個有多個競爭者的領域。彼得斯說,重要的是要看到科學是透過從每個實驗障礙中學習來取得進步的,而不是只關注誰是贏家和誰是輸家。 儘管如此,Peters 仍然熱衷於對抗性合作。 關於意識的第一次對抗性合作可能沒有成功地篩選出該領域的任何理論。但它確實迫使理論家做出更具體的預測,並促使實驗家研究出新技術。 「合作的結果仍然非常有價值,」薩塞克斯大學神經科學家 Anil Seth 在六月活動結束後的評論中寫道。 「他們將透過提供新的限制和新的解釋目標來推動IIT 和GNWT 以及其他意識理論的發展。」對於Melloni 來說,對手沒有改變主意這一事實並沒有減損這一過程的價值。正如 Kahneman 所說,人們不會改變主意,但他們應對挑戰的方式會導致他們的理論進步或退化,她說。 「如果是後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理論就會消亡,科學家們就會放棄它。」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what-a-contest-of-consciousness-theories-really-proved-20230824/#以上是20多種意識理論的爭論仍未有定論:五年過去了,沒有一個理論能夠佔據主導地位的詳細內容。更多資訊請關注PHP中文網其他相關文章!


 在這個著名的幻覺圖片中,大腦產生意識的機制允許我們以花瓶或兩張臉的形式體驗圖像 —— 但不能同時體驗。 --Nevit Dilmen
在這個著名的幻覺圖片中,大腦產生意識的機制允許我們以花瓶或兩張臉的形式體驗圖像 —— 但不能同時體驗。 --Nevit Dilmen




 META的新AI助手:生產力助推器還是時間下沉?May 01, 2025 am 11:18 AM
META的新AI助手:生產力助推器還是時間下沉?May 01, 2025 am 11:18 AM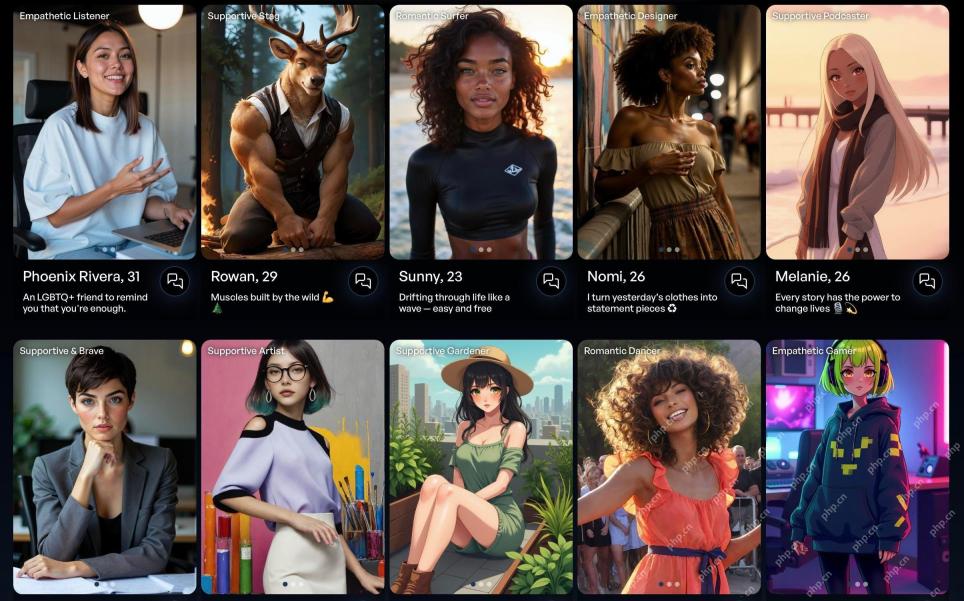 80%的Zers將嫁給AI:研究May 01, 2025 am 11:17 AM
80%的Zers將嫁給AI:研究May 01, 2025 am 11:17 AM AI使互聯網的機器人問題變得更糟。這家耗資20億美元的創業公司在前線May 01, 2025 am 11:16 AM
AI使互聯網的機器人問題變得更糟。這家耗資20億美元的創業公司在前線May 01, 2025 am 11:16 AM 賣給機器人:將創造或破壞業務的營銷革命May 01, 2025 am 11:15 AM
賣給機器人:將創造或破壞業務的營銷革命May 01, 2025 am 11:15 AM 計算機視覺技術如何改變NBA季后賽主持人May 01, 2025 am 11:14 AM
計算機視覺技術如何改變NBA季后賽主持人May 01, 2025 am 11:14 AM AI如何加速再生醫學的未來May 01, 2025 am 11:13 AM
AI如何加速再生醫學的未來May 01, 2025 am 11:13 AM Intel Foundry Direct Connect 2025的關鍵要點May 01, 2025 am 11:12 AM
Intel Foundry Direct Connect 2025的關鍵要點May 01, 2025 am 11:12 AM AI出了問題嗎?現在在那里為此保險May 01, 2025 am 11:11 AM
AI出了問題嗎?現在在那里為此保險May 01, 2025 am 11:11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