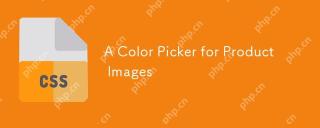1994年,網絡從學術界的陰影中出來並進入了每個人的屏幕。特別是,這是1994年12月第二週的下半年,在三個事故中結束了這一年。
全球網絡財團的成員於12月14日(星期三)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張桌子上擠滿了人。大約二十個人參加了會議,主要科技公司,瀏覽器製造商和基於Web的初創公司的代表。他們在那裡討論網絡的公開標準。
正確完成後,標准設定了技術lodestar。具有競爭利益和優先事項的公司可以圍繞一套共同的關於技術應如何運作的文檔。共享標準的共識創造了互操作性;競爭是通過用戶體驗而不是技術基礎架構進行的。
在1992年,世界上更常見的世界網絡聯盟(或更常見的W3C)就一直在網絡的創建者蒂姆·伯納斯·李爵士(Tim Berners-Lee)爵士所在。計算機科學的麻省理工學院實驗室很快成為了他最熱情的盟友。經過多年的工作,伯納斯·李(Berners-Lee)於1994年10月離開了CERN的工作,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經營該財團。他無意成為獨裁者。他對網絡方向有強烈的看法,但他仍然傾向於聽。
在議程上 - 在桌子上清理了一些基本介紹之後,是一長串需要製定的行政細節。財團的作用,其自身的行為方式以及其對更廣泛網絡的責任僅在會議開始時就概述了。 25名左右的成員逐漸瀏覽了名單。會議結束時,該小組對網絡標準的未來有信心。
第二天,12月15日,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和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宣布了最近更名為Netscape Navigator 1.0版。它已經在Beta中銷售了幾個月,但是那個星期四標誌著更廣泛的發布。為了競標不斷增長的市場,它最初是免費贈送的。幾個月後,在版本1.1發布後,Netscape將被迫向後走。無論哪種情況,瀏覽器都是商業和技術的成功,可以提高之前瀏覽器的速度,可用性和功能。
12月16日,星期五,W3C經歷了第一次挫折。 Berners-Lee絕不意味著MIT成為財團的獨家場所。他計劃為網絡的發源地和一些最偉大的倡導者的家園塞恩(Cern)成為該組織的歐洲主持人。然而,12月16日,CERN批准了其大型強子對撞機的大量預算,迫使他們轉移優先級。重新集中的預算幾乎沒有直接互聯網實驗的空間,而不是直接促進粒子物理學的中心項目。
CERN將不再是W3C的歐洲主持人。一切都沒有丟失。幾個月後,W3C在法國國家計算機科學與控制研究所或InriA研究所成立。到1996年,還將建立在日本基奧大學的第三個地點。
這不是一個離群值,這不是W3C有史以來的最後一次挫折,也不是它將克服的。
1999年,Berners-Lee在題為《編織網絡》的書中發表了網絡創作的自傳說明。這是一個簡潔甚至歷史,在網絡第一十年的主要里程碑中漫步。在整本書中,他經常回到W3C的主題。
他首先是妥協的第一和最重要的框架。 “對我來說,經營該財團始終是一種平衡行為,在花時間保持開放度和以技術的速度速度前進之間,這將永遠是一種平衡行為。”在共享兼容性與較短和較短的瀏覽器釋放週期之間達到平衡將成為W3C的主要目標。
他承認,網絡標準因緊張而蓬勃發展。標準是在分歧和勞力討價還價的中發展的。伯納斯·李(Berners-Lee)在W3C創建之前回想起一段時間,並指出了標準過程如何反映網絡的結構。他寫道:“這些緊張局勢將使財團成為Weblike和Treelike社會結構的相對優點的遺囑理由,”他寫道,“我渴望開始實驗。”然而,由妥協和由緊張定義的網絡財團並不是伯納斯·李的第一個計劃。
1992年3月,Berners-Lee飛往聖地亞哥參加了互聯網工程工作組或IETF的會議。 IETF創建於1986年,為互聯網制定標準,從網絡到路由再到DNS。 IETF標準是無法執行的,並且完全自願。他們沒有受到任何世界政府或受任何法規的批准。沒有實體必須使用它們。取而代之的是,IETF依賴於一個簡單的自負:互操作性對每個人都有幫助。數十年來一直足以維持該組織。
因為一切都是自願的,所以IETF是由迷宮的一組規則和儀式過程來管理的,這些規則和儀式過程可能難以理解。沒有正式會員資格,儘管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用自己的話來說,它沒有“沒有會員,也沒有會費”)。每個人都是志願者,沒有人獲得報酬。該小組每年在轉移地點親自見面。
IETF以一種稱為粗糙共識的原則(通常是運行代碼)運行。有爭議的提案不是正式的投票程序,而是需要達成一定的同意,即大多數(如果沒有的話),技術工作組中的成員都同意。工作組成員決定何時達成共識,其標準逐年轉變為小組。在某些情況下,IETF已轉向嗡嗡聲以達到房間的溫度。 “例如,當我們舉行面對面的會議……而不是一場表演時,有時椅子會要求雙方嗡嗡作響,要么在一個特定的問題上,要么“'或“反對”。 ”
伯納斯·李(Berners-Lee)於1992年3月首次到達IETF。 3月,他被告知他需要在6月舉行的一次會議,以正式提出工作組。在他開始的一年半後,他說服了IETF建立了這三個。
粗糙共識的過程可能很慢。相比之下,網絡重新定義了快速的外觀。新一代的瀏覽器在幾個月後而不是幾年。這是在Netscape和Microsoft參與之前。
網絡的發展在伯納斯 - 李的影響力領域之外螺旋式化。 Inline圖像 - 可能是該網絡成功造成的最大的功能 - 是大學實驗室地下室的小吃和蘇打水的深夜集思廣益的產物。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將其發佈到www-talk郵件列表中時,伯納斯·李(Berners-Lee)在其他所有人都這樣做的時候就了解了這件事。
緊張。 Berners-Lee知道會來的。他曾希望,例如,他的圖像可能會有所不同(“蒂姆在93年夏天為我添加圖像添加了圖像,”安德森(Andreessen)稍後會說),但網絡不是他的。不是任何人。他是這樣設計的。
憑藉其所有規則和儀式,IETF似乎並不適合Web標準。在大學和研究實驗室的私人討論中,Berners-Lee開始探索一條新的道路。像網絡中的利益相關者聯盟一樣,這是一系列創建瀏覽器,網站和軟件的公司的集合 - 可以共同同意對自己達成共識的共識。到1993年底,他在W3C上的工作已經開始。
惠普·帕卡德(Hewlett-Packard)經驗豐富的研究員戴夫·拉格特(Dave Raggett)對網絡有不同的看法。他不是來自學術界,也沒有從事瀏覽器(無論如何還沒有)。他幾乎本能地理解了網絡的實用性是商業軟件。不像是數字電話簿,更像是蘋果公司大成功的Hypercard應用程序。
Raggett無法說服他的老闆對網絡的承諾,因此使用了百分之十的時間,允許其員工從事獨立研究開始與網絡合作。他將自己固定在社區,這是www-talk郵件列表的積極成員,並在IETF會議上定期出席。在1992年秋天,他有機會與Cern的Berners-Lee一起參觀。
大約在這個時候,他遇到了尤里·魯賓斯基(Yuri Rubinsky),他是標准通用標記語言的熱情倡導者,即HTML最初基於的語言。魯賓斯基認為,HTML的局限性可以通過更嚴格的SGML標準來解決。他已經開始了將SGML帶入網絡的運動。拉格特同意了 - 但要點。他還沒有準備好與HTML斷開聯繫。
每次Mosaic都發行了新版本或發布新版本時,原始HTML規範與真實世界網絡擴大之間的差距。 Raggett認為需要更全面的HTML記錄。他開始製作增強版的HTML,以及瀏覽器以演示其功能。它的工作標題是HTML。
Ragget的工作很快開始溢出到他的家庭生活中。他大部分晚上都在一台大型計算機上度過,該計算機佔據了餐桌的相當一部分,與紙,蠟筆,樂高積木和孩子留下的半食餅乾的碎片分享了略帶粘性的表面。 ”經過一年的時間,Raggett有了HTML版本的HTML準備在1993年11月進行。他對語言的改進遠非膚淺。他設法添加了所有已進入瀏覽器的小東西:桌子,帶有字幕和圖形的圖像以及高級形式。
幾個月後,即1994年5月,開發人員和網絡愛好者從世界各地旅行,來到了一些與會者中半場開玩笑地稱為“網絡的伍德斯托克”,這是CERN員工和網絡先驅者Robert Calliau組織的第一次官方網絡會議。在大聲疾呼的800人中,日內瓦的空間只能擁有350人。許多人首次開會。網絡歷史學家馬克·韋伯(Marc Weber)後來形容:“每個人都在刻苦大廳,”“以相同的面對面的實際人的感覺使他們只是在電子郵件或www-talk [sic]郵件列表中的名字。”
它是在網絡站在普遍存在的懸崖上的那一刻。馬賽克團隊中沒有人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幾個月後,他們擁有自己的競爭會議設定),但是已經有關於Mosaic Alum Marc Andresseen的新商業瀏覽器的傳聞,後來被稱為Netscape Navigator。同時,馬賽克已經開始許可其瀏覽器以供商業用途。雅虎的早期版本!隨著越來越多的出版物的成倍增長,例如GNN,WIRED,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上網。
另一方面,IETF的進展很慢。它太細緻了,太確切了。同時,像Mosaic這樣的瀏覽器開始添加他們想要的一切,尤其是HTML。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由馬賽克支撐的標籤,網站創建者被迫在尖端技術和與其他瀏覽器的兼容性之間進行選擇。許多人選擇了前者。
HTML是會議上對話的最大話題。但是另一個亮點是,丹·康諾利(Dan Connolly)是一位在超級計算機製造商凸的年輕,“紅頭髮,海軍切割的德克薩斯人”的舞台。他發表了一個名為“互操作性:為什麼每個人都獲勝的演講”。後來,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次演講,Connolly將成為IETF HTML工作組的主席。
在一個有先見之明的時刻捕捉房間的精神,當HTML的語言破裂時,Connolly描述了未來。當每個瀏覽器都實施自己的HTML標籤以使競爭對手挑戰時。他總結說,該解決方案是能夠在瀏覽器開發速度發展的HTML標準。
Ragget的HTML為成為該標準提供了有力的理由。它詳盡地描述了像馬賽克這樣的瀏覽器中使用的新的HTML,以近乎完美的細節。康諾利後來說:“我一直是極簡主義者,你可以用來完成。兩人達成了協議。 Raggett將繼續通過HTML工作,而Connolly專注於更狹窄的升級。
Connolly的版本很快將成為HTML 2,並且在來回一年後,在IETF進行了粗糙的共識建築,它成為官方標準。它幾乎沒有HTML的細節,但是Connolly能夠正式記錄瀏覽器多年來支持的功能。
Ragget的提議將其更名為HTML 3,被卡住了。為了適應不斷擴展的網絡,它的尺寸繼續增長。 “要在150頁的草稿上達成共識,並且每個人都想發表意見是樂觀的,至少可以說,”拉格特後來坦率地說道。但是到那時,Raggett已經在W3C工作,HTML 3很快就會成為現實。
伯納斯·李(Berners-Lee)也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次網絡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並以主題演講結束了。他沒有具體提及W3C。相反,他專注於網絡的角色。他後來寫道:“在場的人現在是創建網絡的人,因此,唯一可以確定生產的系統適合合理且公平的社會的人。”
1994年10月,他著手為網絡創造更公平,更容易獲得的未來。全球網絡財團已正式宣布。伯納斯·李(Berners-Lee)與少數員工一起加入了這份名單,其中包括戴夫·拉格特(Dave Raggett)和丹·康諾利(Dan Connolly)。兩個月後,即1994年12月第二週的下半年,W3C成員首次開會。
在會議之前,伯納斯·李(Berners-Lee)對W3C的工作方式有粗略的草圖。任何公司或組織都可以加入,因為他們支付會員費,這是與該公司規模相關的分層定價結構。會員組織將派代表參加W3C會議,以提供創建標準的進一步的意見。通過將W3C程序限制在付費成員的情況下,Berners-Lee希望將對話集中在Web技術的現實世界實施到對話。
然而,儘管有封閉的會員資格,但W3C在可能的情況下開放。會議記錄和文件向公眾中的任何人開放。作為新標準實驗的一部分編寫的任何代碼都是可以自由下載的。
W3C成員聚集在麻省理工學院,下一步必須決定其標準將如何工作。他們決定進行一個僅停止粗略共識的過程。儘管它們通常被稱為標準,但W3C並未為網絡創建官方標準。在W3C上創建的技術規格是最終形式,作為建議。
實際上,它們是建議。他們詳細概述了技術的工作原理。但是他們留下了足夠的開放,以便瀏覽器可以準確弄清實施方式的工作原理。 W3C Sally Khudairi的前通信負責人曾經對W3C的通信負責人表示:“ W3C的目的是確保網絡的解釋性,並且在遠距離現實的遠距離中。
初始草稿在W3C及其成員之間創建一個反饋循環。它們提供了有關Web技術的指導,但是即使規範在起草過程中,瀏覽器也開始介紹它們,並鼓勵開發人員對其進行試驗。每次發現問題時,都會修訂草案,直到達成足夠的共識為止。那時,草稿成為建議。
總是會有緊張局勢,而伯納斯·李(Berners-Lee)很好地知道。訣竅不是試圖抵抗它,而是創建一個成為資產的過程。這就是建議的預期效果。
1995年底,IETF HTML工作組被新創建的W3C HTML編輯審查委員會所取代。 HTML 3.2將是W3C完全基於Ragget的HTML發布的第一個完全由W3C發布的HTML版本。
1997年,網絡開發中有一年的時間,當時瀏覽器擺脫了W3C的暫時建議。 Microsoft和Netscape開始發布一套新的功能,與商定的標準分開。他們甚至為他們起了名字。他們稱他們為動態HTML或DHTML。他們幾乎將網絡分為兩分。
DHTML最初是慶祝的。動態意味著流體。 HTML初始惰性狀態的自然演變。換句話說,網絡活著。
吹捧它的功能,1997年《連線》中的一項功能稱DHTML為“魔術魔杖網絡嚮導長期以來一直在尋求”。在對新技術的熱情中,它很少有人注意到,“ Microsoft和Netscape憑藉其標準機構的工作,特別是在引入級聯樣式表或CSS的引入,但大多數功能都被添加了“不考慮兼容性不大。 ”
當地的事實是,使用DHTML需要針對一個瀏覽器或另一個瀏覽器,Netscape或Internet Explorer。一些開發人員選擇簡單地選擇一條路徑,在其網站底部拍打橫幅,該橫幅顯示為“最佳觀看……”一個瀏覽器或另一個瀏覽器。其他人完全忽略了該技術,希望避免其糾結的複雜性。
當然,瀏覽器有其原因。開發人員和用戶要求官方HTML規範中未包含的內容。正如一位Microsoft代表所說,“為了將新技術推向標準機構,您必須繼續創新……我對我的客戶負責,而Netscape的人也是如此。”
一個更具動態的網絡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是一個碎網的網站是站不住腳的。對於某些開發人員來說,這將被證明是最後的稻草。
HTML 3.2發布並隨著瀏覽器的快速發展後,HTML編輯審查委員會分為三個部分。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立於其他責任的責任領域。
勞倫·伍德(Lauren Wood)博士成為文檔對像模型工作組的主席。伍德是前理論上的核植物學家,曾是Softquad的產品技術總監,Softquad是SGML倡導者尤里·魯賓斯基(Yuri Rubinsky)創立的Comapny。在那裡,她幫助製作了HTML HTML編輯器。 DOM規格為瀏覽器創建了一種實現動態HTML的標準化方法。伍德描述它的描述方式是:“您需要一種將數據和程序綁在一起的方法,而文檔對像模型就是那種膠水。”她在文檔對像模型和後來的XML上的工作將對網絡產生持久的影響。
級聯風格的工作組工作組由克里斯·利利(Chris Lilley)主持。 Lilley的背景是計算機圖形學,是曼徹斯特大學計算機圖形學院的老師和專家。 Lilley曾在IETF上在HTML 2規格上工作,以及便攜式網絡圖形(PNG)的規範,但這將標誌著他首次擔任工作組主席。
CSS在1997年仍然是一個相對的新人。它已經進行了多年的工作,但尚未有重大釋放。 Lilley將與CSS的創建者(HåkonLie和Bert Bos)一起工作,以創建第一個CSS標準。
最後的工作組是為HTML的,在丹·康諾利(Dan Connolly)的主持下,繼續他的位置。康諾利(Connolly)幾乎和伯納斯·李(Berners-Lee)那樣在網絡上。他是1991年10月觀看的人之一,當時伯納斯·李(Berners-Lee)在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的超文本會議上為一小群不受影響的人演示了網絡。實際上,正是在那次會議上,他第一次遇到了那個女人,後來成為他的妻子。
他回到家後,他嘗試了網絡。一個月後,他給伯納斯·李(Berners-Lee)發了電話。這只是三個詞:“您需要DTD。”
當Berners-Lee開發HTML的語言時,他從前任SGML借用了其慣例。 IBM在1970年代初期開發了廣義的標記語言(GML),以使打字員更容易創建格式化的書籍和報告。但是,它很快就失控了,因為人們會採取捷徑並使用他們想要的任何版本的標籤。
那時他們開發了文檔類型的定義,或者按照Connolly所說的DTD。 DTD是將“ S”(標準化)添加到GML中的原因。使用SGML,您可以為數據,其方案及其結構創建一組標準化的指令,以幫助計算機了解如何解釋它。這些說明是文檔類型的定義。
從版本2開始,Connolly向HTML添加了類型定義。它將語言限制在一組較小的商定標籤上。實際上,瀏覽器將其視為一個寬鬆的定義,繼續實現自己的DHTML功能和標籤。但這是第一步。
1997年,HTML工作組(現為W3C內部)開始進行HTML的第四次迭代。它擴展了語言,增加了規格,更高級的功能,複雜的表格和表單,更好的可訪問性以及與CSS的更定義的關係。但是它也將HTML從單個模式分為三個不同的文檔類型定義,以供瀏覽器採用。
第一個是框架集,通常不使用。第二個是過渡性的,包括過去的錯誤。它擴展了更大的HTML子集,其中包括瀏覽器多年來使用的非標準,呈現HTML,例如和
第三個DTD被稱為嚴格。根據嚴格的定義,HTML僅被削減到其標準的非代表性特徵。它刪除了Netscape和Microsoft引入的所有唯一標籤,僅留下結構化元素。如果您今天使用HTML,則可能會在同一標籤基礎上繪製。
嚴格的定義在沙子上繪製了一條線。它說,這是HTML。它最終為開發人員提供了一次為每個瀏覽器編碼的方法。
在1998年8月的《 Computerworld》(Computerworld)中,即即將到來的Y2K末日的大型功能之間,在萬維網上計費的潛力以及對微軟的反托拉斯擔心 - 是一個小公告。它的標題閱讀, “瀏覽器標準針對的。”這是關於建立一個新的基層網絡開發人員組織,旨在為瀏覽器帶來網絡標準支持。它被稱為Web標準項目。
該項目的共同創建者格倫·戴維斯(Glenn Davis)在公告中引用了。 “問題在於,隨著瀏覽器的每一代,瀏覽器製造商與標準支持的分歧更遠。”多年來,開發人員被迫為不同的瀏覽器編寫不同的代碼,已經足夠了。在郵寄列表中進行了一些偏僻的對話,已經旋轉成一個完全成長的動作。在發布會上,已經有450名開發人員和設計師註冊了。
戴維斯對網絡並不陌生,他理解了它的挑戰。他在網絡上的第一次經歷可以追溯到1994年,就在馬賽克(Mosaic)首次引入直列圖像之後,當他創建了當天的畫廊網站酷網站時。每天,他都會在一個有趣的或前衛或實驗網站上提供一個主頁。對於仍然很小的網頁設計師社區,這是一個即時的熱門單曲。
除了戴維斯認為值得推出的網站外,沒有其他標準。 “我一直在尋找推動極限的事情,”他後來定義它。戴維斯(Davis)幫助重新定義了早期網絡的期望,使用綽號酷作為速記,涵蓋許多可能性。 Dot-Com設計作者兼媒體教授**梅根·安克森(Megan Ankerson)指出了什麼“這個涼爽網站的生態系統朝著網絡範圍的範圍示意的是:它的時間和空間脫位,其與主流媒體的區別和擴展的區別,它的承諾是自我出版的工具,以及自我出版的工具,以及令人難以置信的個人,Mundorrordrane和Extrulordrorminare'''在網上一段時間裡,戴維斯一直是Cool的仲裁者。
隨著時間的流逝,戴維斯將他的網站轉變為Project Cool ,這是創建網站的資源。在DHTML時代,戴維斯(Davis)的Project Cool Tutorials提供了充分利用網絡的建設性和實用技術。他的寫作大量致力於解釋如何編寫Netscape Navigator和Microsoft的Internet Explorer中使用的代碼。最終,他和其他許多人都達到了一個突破點。 1997年底,Netscape和Microsoft都以斑點標準支持發布了4.0瀏覽器。很明顯,即將發布的5.0版本正計劃進一步傾向於不均勻和矛盾的DHTML擴展。
戴維斯(Davis)用盡了耐心,幫助喬治·奧爾森(George Olsen)和杰弗裡·澤爾德曼(Jeffrey Zeldman)建立了郵件列表。該清單始於二十個人,但很快就獲得了支持。 Web標準項目(稱為WASP)於1998年8月正式從該列表正式推出。它始於計算機世界等雜誌上的數百名成員和公告。在幾個月內,它將有成千上萬的成員。
黃蜂的策略是將瀏覽器(將瀏覽器公開地推向網絡標準支持)。黃蜂並不是要成為雙曲線的名字。 ” W3C建議無法執行標準。
Zeldman是著名的設計師和標準倡導者,將對網絡製造商產生持久的影響。後來,他將在最具影響力的幾年中運行黃蜂。他的網站和郵件列表(分開的列表)將成為關心Web標準並使用最新Web技術的設計師的聚會場所。
在十年半的任期內,黃蜂會改變焦點幾次。他們推動瀏覽器更好地利用HTML和CSS。他們教開發人員如何編寫基於標準的代碼。他們主張提供更大的可訪問性和工具,以支持開箱即用的標準。
但是,他們的任務在發布的第一天發佈到他們的網站上,永遠不會動搖。 “我們的目標是支持這些核心標準,並鼓勵瀏覽器製造商也這樣做,從而確保所有人的簡單,負擔得起的網絡技術訪問。”
黃金生物很早就成功地完成了任務。一些瀏覽器,尤其是歌劇,一開始就使用了標準。他們的努力受到黃蜂的稱讚。但是,共同構成大多數Web使用的兩個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和Netscape Navigator)將需要一些工作。
1998年向AOL出售40億美元的銷售不足以讓Netscape與Microsoft競爭。 Netscape 4.0發布後,他們以粗體策略進行了翻倍,選擇將整個瀏覽器的代碼作為Mozilla項目下的開源發布。每天的消費者都可以免費下載;鼓勵編碼人員直接做出貢獻。
社區成員很快在Mozilla注意到了一些東西。它有一個新的渲染引擎,通常稱為壁虎。與計劃的Netscape 5的計劃發行版本不同,該版本充其量提供了標準支持,Gecko支持了HTML 4和CSS的相當完整版本。
WASP將其強大的成員轉移到將Netscape推入將Gecko推入其下一個主要版本中的任務。一種熟悉的黃蜂策略被稱為障礙。它的一些成員在Hotwired和CNET等出版物中工作。黃蜂會立即批評幾個媒體上的文章,例如,面對壁虎的一個完全合理的解決方案,Netscape忽略了標準。通過這樣做,他們通常能夠吸引至少一個新聞周期的注意力。
黃蜂還採取了更直接的行動。要求成員向瀏覽器發送電子郵件,或簽署請願書,以表明對標準的廣泛支持。開發人員的壓力壓力偶爾足以將瀏覽器推向正確的方向。
部分原因是黃蜂同意將壁虎成為5.0版的一部分。 Netscape 5的Beta版本確實將具有符合標準的HTML和CSS,但它被其他地方的問題所困擾。釋放將需要數年的時間。那時,微軟在瀏覽器市場上的統治將接近完成。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微軟更加隔離基層壓力。與科技巨頭有關,黃蜂的現場戰術事實證明是不太成功的。
但是在微軟的牆壁內,黃蜂至少有一個忠實的追隨者,開發商Tantekçelik。 Çelik在他的網絡職業生涯的延伸時就不懈地在網絡標準方面進行了鬥爭。後來,他將成為WASP指導委員會的成員,並成為W3C多個工作組的代表,直接從事標準的製定。
Çelik在Internet Explorer內為Mac跑了一個團隊。儘管它以其更加普遍的Windows對應方式共享了一個名稱,品牌和一般功能,但Mac在單獨的代碼庫上運行。 Çelik的團隊主要留在了一個巨大的組織中,其其他優先事項在瀏覽器上工作的其他優先事項不多,而瀏覽器沒有很多人使用。
由於瀏覽器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留給了他,Çelik開始在Web技術的最前沿與舊金山的Web設計師聯繫。通過運氣,他與Web標準項目的幾個成員建立了聯繫。他會和他們一起訪問,問他們想在Mac IE瀏覽器中看到什麼。 “答案:更好的標準支持。”
他們幫助Çelik意識到他在較小的瀏覽器上的工作可能會產生影響。如果他能夠支持標準,因為它們是W3C定義的,它可以作為設計師正在編寫的代碼的基準。換句話說,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擔心IE的Windows和Netscape中的Buggy標準。他們不需要擔心Mac的IE。
Çelik需要聽到的全部。當Internet Explorer 5.0用於2000年推出的MAC時,它在全面支持Web標準時得到了支持; HTML, PNG images, and most impressively, one of the most ambitious implementations of the new Cascading Style Sheets (CSS) specification.
It would take years for the Windows version to get anywhere close to the same kind of support. Even half a decade later, after Çelik left to work at the search engine Technorati, they were still playing catch-up.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the W3C found themselves at a fork in the road. They looked to their still-recent past and saw it filled with contentious support for standards — Incompatible browsers with their own priorities. Then they looked the other way, to their towering future. They saw a web that was already evolving beyond the confines personal computers. One that would soon exist on TVs and in cell phones and on devices we that hadn't been dreamed up yet in paradigms yet to be invented. Their past and their future were incompatible. And so, they reacted.
Yuri Rubinsky had an unusual talent for making connections. In his time as a standards advocate, developer, and executive at a major software company, he had managed to find time to connect some of the web's most influential proponents. Sadly, Rubinsky died suddenly and at a young age in 1996, but his influence would not soon be forgotten. He carried with him an infectious energy and a knack for persuasion. His friend and colleague Peter Sharpe would say upon his death that in “talking to the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ho knew Yuri, there was a common theme: Yuri had entered their lives and changed them forever.”
Rubinsky devoted his career to making technology more accessible. He believed that without equitable access, technology was not worth building. It motivated all of the work he did, including his longstanding advocacy of SGML.
SGML is a meta-language and “you use it to build your own computer languages for your own purposes.” If you hand a document over to a computer, SGML is how you can give that computer instructions on how to understand it. It provides a standardized way to describe the structure of data — the tags that it uses and the order it is expected in. The ownership of data, therefore, is not locked up and defined at some unknown level, it is given to everybody.
Rubinsky believed in that kind of universal access, a world in which machines talked to each other in perfect harmony, passing sets of data between them, structured, ordered, and formatted for its users. His company, SoftQuad, built software for SGML. He organized and spoke at conferences about it. He created SGML Open, a consortium not unlike the W3C. “SGML provides an internationally standardized, vendor-supported, multi-purpose, independent way of doing business,” was how he once described it, “If you aren't using it today, you will be next year.” He was almost right.
He had a mission on the web as well. HTML is actually based on SGML, though it uses only a small part of it. Rubinsky was beginning to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members of the W3C, like Berners-Lee and Raggett, about bring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version of SGML to the web. He was even writing a book called SGML on the Web before his death.
In the hallways of conferences and in threaded mailing lists, Rubinsky used his unique propensity for persuasion to bring people several people together on the subject, including Dan Connolly, Lauren Wood, Jon Bosak, James Clark, Tim Bray, and others. Eventually, those conversations moved into the W3C. They formed a formal working group and, in November of 1996,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 was formally announced, and then adopted as a W3C Recommendation. The announcement took place at an annual SGML conference in Boston, run by an organization where Rubinsky sat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XML is SGML, minus a few things, renamed and repackaged as a web language. That means it goes far beyond the capabilities of HTML, giving developers a way to define their own structured data with completely unique tags (eg, an
XML was appealing to the maintainers of HTML, a language that was beginning to feel somewhat complete. “When we published HTML 4, the group was then basically closed,” Steve Pemberton, chair of the HTML working group at the time,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Six months later, though, when XML was up and running, people came up with the idea that maybe there should be an XML version of HTML.” The merging of HTML and XML became known as XHTML. Within a year, it was the W3C's main focus.
The first iterations of XHTML, drafted in 1998, were not that different from what already existed in the HTML specifications. The only real difference was that it had stricter rules for authors to follow. But that small constraint opened up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and XHTML was initially celebrated. The Web Standards Project issued a press release on the day of its release lauding its capabilities, and developers began to make use of the stricter markup rules required, in line with the work Connolly had already done with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s.
XHTML represented a web with deeper meaning. Data would be owned by the web's creators. And together, computers and programmers, could create a more connected and understandable web. That meaning was labeled semantics. The Semantic Web would become the W3C's greatest ambition, and they would chase it for close to a decade.
Subsequent versions of XHTML would introduce even stricter rules, leaning harder into the structure of XML. Released in 2002, the XHTML 2.0 specification became the language's harbinger. It removed backwards compatibility with older versions of HTML, even as Microsoft's Internet Explorer — the leading browser by a wide margin at this point — refused to support it. “XHTML 2 was a beautiful specification of philosophical purity that had absolutely no resemblance to the real world,” said Bruce Lawson, an HTML evangelist for Opera at the time.
Rather than uniting standards under a common banner, XHTML, and the refusal of major browsers to fully implement it, threatened the split the web apart permanently. It would take something bold to push web standards in a new direction. But that was still years away.
Enjoy learning about web history with stories just like this? Jay is telling the full story of the web, with new stories every 2 weeks. Sign up for his newsletter to catch up on the latest... of what's past.
以上是第7章:標準的詳細內容。更多資訊請關注PHP中文網其他相關文章!
 瀏覽器引擎多樣性Apr 16, 2025 pm 12:02 PM
瀏覽器引擎多樣性Apr 16, 2025 pm 12:02 PM當他們在2013年去Chrome時,我們失去了歌劇。與Edge今年早些時候也進行了同樣的交易。邁克·泰勒(Mike Taylor)稱這些變化為“減少
 每周平台新聞:Apple部署網絡組件,漸進的HTML渲染,自託管關鍵資源Apr 16, 2025 am 11:55 AM
每周平台新聞:Apple部署網絡組件,漸進的HTML渲染,自託管關鍵資源Apr 16, 2025 am 11:55 AM在本週的綜述中,Apple進入Web組件,Instagram如何插入腳本以及一些思考的食物,以進行自託管關鍵資源。


熱AI工具

Undresser.AI Undress
人工智慧驅動的應用程序,用於創建逼真的裸體照片

AI Clothes Remover
用於從照片中去除衣服的線上人工智慧工具。

Undress AI Tool
免費脫衣圖片

Clothoff.io
AI脫衣器

AI Hentai Generator
免費產生 AI 無盡。

熱門文章

熱工具

MantisBT
Mantis是一個易於部署的基於Web的缺陷追蹤工具,用於幫助產品缺陷追蹤。它需要PHP、MySQL和一個Web伺服器。請查看我們的演示和託管服務。

SAP NetWeaver Server Adapter for Eclipse
將Eclipse與SAP NetWeaver應用伺服器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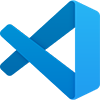
VSCode Windows 64位元 下載
微軟推出的免費、功能強大的一款IDE編輯器

SublimeText3 英文版
推薦:為Win版本,支援程式碼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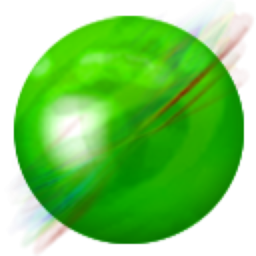
ZendStudio 13.5.1 Mac
強大的PHP整合開發環境